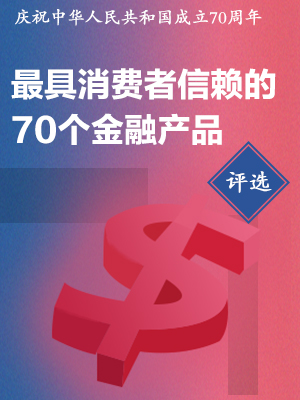金融作家 | 陈杨:笔底烟水,心上菩提
来源: 中国金融网 2025-08-15 10:54:40

淫雨霏霏的八月,寂寥如宣纸上未干的留白,偶然间撞进纪录片《古道清凉》里的镜头。居士们扛着摄像机跟拍了五年,镜头里的大悲寺僧人总在晨露中赶路,粗布僧袍上的补丁像层层叠叠的年轮,风穿过袖管的破洞,竟有了徽州老宅飞檐铜铃的清响 —— 不惹尘埃,只应天地。
苦行僧的脚印落在山川田野间,像一行行不用墨写的诗。忽然间明白:人这一辈子,都在苦苦追寻,追寻一种值得托付生命的东西。于他们是袈裟里的戒律,于我,便是笔尖与灵魂相触的刹那。
没有电风扇的童年,夜晚酷热难耐,总爱把双腿泡在盛满井水的木桶里,趴在原木的方桌上写写画画。井水的清凉混着笔尖的炽热,比现在洋房中央空调的冷风更能浇透心魂。那时还不懂啥叫“精神支柱”,只知道趴在木桌上,蚊虫的嗡鸣、窗外的蝉噪都成了伴奏,铅笔划过毛边稿纸的沙沙声,比母亲轻摇蒲扇的微风更让人舒心。
冬日里便蜷缩在木制的火桶上,手指冻得像红萝卜,哈着气写下的句子歪歪扭扭,却透着炭火的余温。长大后才明白,那些在苦难日子里不肯放下的笔,原是在为孤独的灵魂搭一间遮雨的茅庐,让生命在困顿时仍能保持千年胡杨般向上的弧度。
黄沙漫天的冬日,苦行僧们在干涸的沟渠里用膳,昏暗的日光照在清瘦的脸上,比鎏金佛像多了几分人间的虔诚。乞食遇着质疑的目光,他们垂眸一笑,那淡然里藏着的干净,比天目山的清泉更透亮。不碰金钱的戒律像根绷紧的弦,在物欲横流里弹出清越的音——原来信仰从不在香火鼎盛处,只在心头那点笃定的微光里。纵使世风如浪,也能锚定生命的航向。
想起近日少林寺原方丈那被浮名漫漶的背影,像被秋雨打落的残荷,昔日的庄严全浸没在污秽的沼泽地里。真正的修行从不是庙堂高筑,而是乱世里守得住的内心道场。一如写作,在滚滚红尘里寻个安静角落,悄悄筑起自己的精神庙堂,让灵魂在文字的呼吸里,始终保持本真的模样。

初入钢铁国企的矿山岁月,算得上是人生第一重修行。每日里安全巡查分厂,几十里山路全靠脚步去丈量。春天杜鹃花开得泼泼洒洒,便在检查记录背面素描勾勒上几笔;秋日野果落在安全帽上,酸甜的汁水溅到稿纸上,竟让文字有了草木的芳香。那些带着矿石粗糙质感的字句,是我最早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—— 原来文字不必精美、华丽,沾着矿床泥土的温度,便自带钢铁般的力量。
每年刊发的通讯稿件有几十篇,攒到年底的稿费正好换来家人的新衣和孩子的奶粉。那时才懂,文字不光能安放灵魂,还能扛起生活的重量。报纸的墨香比咖啡更醉人,每日盼着副刊上那新鲜出炉的“豆腐块”,像农人盼着田垄上的新苗 —— 精神的成长,原是与柴米油盐相生相伴的。
而立之年,沿着徽商古道的脚印南下。深圳的霓虹灯太亮,晃得人看不清初心。出租屋窗户正对着罗芳路122 号“人保南方大厦”,淡蓝色玻璃幕墙反射着月光,像冰冷的镜子,照见我初来的局促与不安。为赶稿熬过的夜,比罗湖商业街的灯火还稠,胃里的空、指尖的麻,都在键盘声里慢慢淡去。文字成了对抗现实的铠甲,屏幕上跳动的字符,是我在这陌生城市种下的禾苗,得虔诚侍弄,才能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里,长出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孱弱之光。
也有把笔扔在桌上的时候,听它滚落时一声轻叹。闭上眼,故乡青苔石板路、棠樾牌坊群、大悲寺僧人的脚步、年少时木桶里的专注,便一起涌上心头。再拾起笔,大脑变得清醒:写作哪是爱好,分明是母亲的怀抱,父亲的脊梁,是风雨里能让灵魂扎根的土壤,让生命漂泊中始终有处的依靠。
人这一辈子,总得有样东西,比物质持久,比情感坚韧。它能给生命安上坐标,成为抵御岁月侵蚀的永恒力量。于我,这东西便是文字,像梵语中的“般若”,能穿透言语的流变,给生命定下恒定的价值 —— 不是外在的评判,而是内心的澄明。
这份执念早有来头。浙江的表哥带我初识烟雨江南时,便在笔记本扉页上留下了“文字如刻石,需心手相应”的赠言。他常带我去浙大看古籍,指尖划过泛黄书页时说:“你看西泠印社的匠人,一方石印刻上百遍,不是技法不够,是要让石头记住刻刀的温度。”
今年春节,当我带上家人再次来到杭州,才明白了表哥当初的用心,才真正读懂了西湖别样的文字意境。这哪里是一湖淡水?分明是被灵隐寺钟声磨了千年的砚台。晨雾是砚开的墨,柳丝是悬着的笔,雷峰塔的倒影在湖面摇晃,像笔锋未干的撇捺,得等风停后的落定。孤山的青石板上藤蔓爬过了墙,像宣纸上洇开的墨 —— 文字这东西,像表哥说的刻石一样,“宽慢来,弗着急”。
白蛇传里的“情定三生”哪是杜撰?是断桥石板记着的脚印,是雷峰塔砖缝藏着的光阴。最动人的文字,是生命本身在时光里慢慢写就,不必雕琢,自会映出天光云影。

西湖的月总带着三分水汽,落在稿纸上,竟和徽州老宅墙头漏下的清辉重叠了。想来文字的根,早被表哥那两句赠言,悄悄种进了江南水乡。近年发表的文章,像苏堤桃柳般年年抽芽,而《海外文摘》的签约聘书,恰似西泠印社那方刻字的石印,时时提醒来路与去向 —— 所谓一点成就,不过是让初心在岁月里愈发清晰。
有人问我写作的秘诀,总想起大悲寺的僧人—— 行脚时从不多言,专注赶路,一步步脚踏实地往前挪。文字的修行,不是精美辞藻的堆砌,更不是技巧的花哨,只在于日复一日的坚守,让灵魂慢慢沉淀。就像龙井茶在时光的泉水里舒展,熬出最醇厚的甘。这份甘,是对生命本质的洞察,是在喧嚣中守住的那份人间清醒。
空闲时爱在湖边绿道散步,总觉得文字是另一种头陀行。僧人们用脚步丈量山河,我用笔墨记录岁月,原是同一种坚守:在无常中寻找恒常,在流动中锚定静定。诱惑如西湖涟漪,稍不留意就乱了章法,唯有让心沉下去,才能让文字立起来。
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”当灵隐寺钟声掠过水面时,便知该学孤山的梅,耐住苦寒,才得见春天。李叔同抛却津门繁华皈依佛门,才懂得了真正的精神支柱从不是温室盆栽,而是风雪里不肯折腰的枝桠,在岁月里才长得愈发挺拔。一如弘一法师终极追求 —— 不求物质的寡众,只在意自我淬炼中成就的风骨。

罗湖金融街的“人保金融大厦”到“深圳市作协”,直线距离不过两百多米,而我却走了近二十年。七千多个日夜,像西天取经的漫漫长路,今日我方才拿到叩门的“真经”。红岭中路 1038 号那扇文联的门,总怀着敬畏不敢轻推,只静静站着远眺,如朝圣的信徒——原来有些路,用脚走只要片刻,用心走,却需要一生。这一路的跋涉,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终点,而是让生命在坚守中愈发丰盈。
文字于我,早已是心上的菩提。不必焚香,不必敲钟,只在落笔刹那,便知此心归处。“江山留胜迹,我辈复登临。”这人间纵有千般喧嚣、万般诱惑,只要笔尖还能触到纸的温度,灵魂便永远有处可去 —— 那是比江南更温润的故乡,比庙堂更清净的道场,是我用一生守护的,精神的原乡。
作者简介:陈杨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深圳市作协会员,《海外文摘》签约作家,《深圳保险》特约撰稿人,入选“深圳市金融骨干人才培养计划”,现任职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。




 关注金融网
关注金融网